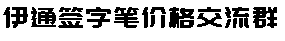王芳,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散文集《彼岸风吹》《聆听遥远的呼吸》《故纸素心》,有多篇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湖南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南方文学》《青年作家》《教师博览》《读者》《青年文摘》等刊物。散文集《彼岸风吹》获得首届三周文艺奖。散文集《聆听遥远的呼吸》获全国第二届社科类普及读物奖。
油彩之下
文丨王芳
这是我第三次尿血了。
最早是我二十岁那年早春,第二次是去岁暮秋,这次则是仲春,相同的是都痛得要人的命,不同的是,病一次比一次来得急,毫无征兆,如山崩海啸,你还在海边嬉戏呢,忽然间它就一浪接一浪扑过来,让你傻看着,忘记后退,整个世界在瞬间都熄了光灭了色,什么人世的情义,生命的理想,那些毕其一生追赶着去实现的东西,完全退到这痛的背后,阴森森地朝你笑。
我当然知道,它不会毫无理由地侵犯我。
春天这样张扬,肆意,刚开始时新叶子把旧叶子挤得掉下来,铺了满地,每天打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抹掉窗户口不小心飘来并未枯黄的几片,后来索性任由它去,直到新的叶子从嫩绿变成放出油光的纯净之色,才肯把堆了一槽和着雨水的叶片儿除去,那时木兰花也从开到败,历了好些风雨,整条街的香樟树上,细细碎碎浅黄色小花不管不顾地散发着清芬,即便是下雨,也要从雨的缝隙里溜一点出来。
偏偏这段时间我梦特别多,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大堤上追赶飞机,飞机呼啸而去,我只能一直站着,气急败坏地看着天,无助地跺着脚;有时是上课要爬很窄很陡的楼梯,好不容易爬上去,才发现走错了教室,此时铃声已响,无法返回;有时是满地的毛毛虫,脚都无处可落;有时是在船上,忽然船就进水沉了,我穿上鞋在水里狂奔,呐喊,茫茫水面无人回应……
以为自己是最懂季节的人,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旋律,而我能随着那些旋律舞动,以为那些映着阳光发出光泽的树,可以让我安宁,可是,无数琐细的事件向我奔来,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侵扰了我的生活。
忙碌?无止境的琐碎的望不到边的忙碌?混乱的生活?不知道目标何在的生活?躁动不安?无所适从?在脑海里搅成一团的各种事件各种情绪?从梦的粘着里拖着疲惫的身子,我看到了新一轮晨曦。
起床啦 !唤身边人。身边人依然酣睡。但上班是争分夺秒的事情,他知道。不出一分钟,他翻了个身,擦着眼叫,给我在衣柜里拿那件蓝格子衬衣!天色依然不明,又怕伤他眼睛,不敢开灯,就着昏暗的晨光,我胡乱拿了一件丢过去。
他摸了摸,不对!你怎么找个衣服都找不到?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
我感到了无法控制的委屈,觉得无论你怎么想温柔以待,他都不愿给你制造温柔的机会。就着这句话,一场火药味越来越足的对话,在这个清晨展开了。
语气越来越不对,一瞬间,有什么推着我冲向他,一脚朝他踹去。动手的是我!事后我无法认出那样一个暴怒的我,像毛发竖起的狮子,样子一定是难看极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在这个毫无信任感的早晨来临。关于这场婚姻的所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我,往日生活中积淀的怨怒的碎片,像电影还原的镜头一般,齐齐向我飞来,我恨不能永远不再见他。爱过又能怎样?终究我们在岁月里变成了各自憎恨的模样。
打理好儿子的早餐,我摔门而出,第一次没有坐他的车去上班。满载着我的恨意的道路居然出奇的清静,在路边等的士,花了近十分钟,结果奔到学校门口时,黄黑相间的车栏正缓缓关上,铃声随之而起,我迟到了。
各种奔袭而来将要完成的任务,无数的事件,正在我脑里轰轰地转,手机信息又响了。瞄一眼,是儿子的班主任老师。我的心“咯噔”一下,手颤抖起来。我知道,好事绝对犯不着发信息。打开一看,“你儿子最近退步很大,请引起重视,如有时间,可放学时来接他,共同教育”。
情绪溃不成军,背起包就冲出了办公室。我一路狂奔,从三楼到了长满爬山虎的办公楼边上,风在我耳边呼呼响,天气闷热,我明显感觉脸上长东西了,一摸,天,两边脸颊有小疙瘩!停下来掏镜子,一照,全是小黄泡!再看镜中的自己,眉头紧锁,目光混浊,肌肉绷紧,很难看。我不能这个样子去见他老师,否则人家以为我要寻仇来了。
返回办公室。肩膀痛起来,好像左腰也出了问题——儿子还没进青春期呢!每天回家,开门第一件事是大叫一声“妈妈!”,然后进房间写作业。因为忙碌,也因为对他的信任,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他的作业也没有辅导过他的功课了,偶尔抽查,见做得很敷衍,命他重写,他总是眉毛倒竖地回答“我不!”,我气极,冲过去就要抢他的作业丢了,他呢,直接用手抓住我,使我无法“行凶”。我气得大喊大叫,历数他的种种不求上进,他也大喊大叫,还直说,“你根本不是一个好妈妈!”就这样,每次冲突都以我极为生气却只能不了了之结局。
这次恶果来了,退步到老师要通知家长的地步。如果自己不是老师,可能还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决定把这事向他爸爸通告一下。一个电话过去,他爸爸没好气地说,孩子的事不都是你在管么?你没见我忙得不可开交?再说了,男孩子有自己的个性,你不要总是大惊小怪!——可是,老师那儿——还有,记得回家做饭,上午四节课呢,饿!电话果断挂。
还没有接触到事件的核心呢,我这儿已经悲愤交加风雨满城。我恨自己在所谓的教育面前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关于一个自命为思想者的尊严!明明知道孩子学的那些东西陈腐不堪,二十几年前我学过的,我反感过的那种种呆板知识和教育的方式,现在又加诸在我儿子的头上,明明清楚我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坏孩子,更多时候他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思考应该得到我的赞赏,明明他是那么富有个性阳光开朗能说会道的少年,明明清楚他甚至不多不少地遗传了我热爱大自然的天性,与小鸡小猫呆一起时灵性十足,,这并不是他的错,偏偏就因为一个成绩,一个在普天之下都无法逃脱的考试面前,我放不过他!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信奉言传身教,我执着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只是想让他知道每一个人都必须靠自己。我错了么?
他爸爸去哪儿了?永远像这一次,他在旁边,就好像与我们隔了一个屏障,他单方向地屏蔽了有我们的世界,超然物外。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一看,是父亲。我的心从深渊落到更深的深渊。
电话那头说,我要来检查病,这几天脸肿得厉害,早晨起来,头要昏上一两个小时,还咳嗽得特别厉害,怕是高血压和冠心病复发,又怕像前年一样引起支气管扩张吐血,已经在路上,不久便到。
我开始手脚冰凉。自前年血泊中的抢救,长达一月的陪护以来,父亲主动打来的电话总是让我胆颤心惊,给他设置的独特的铃声使我成了惊弓之鸟。事实证明,一向并不愿惊扰孩子的父亲,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父亲的电话刚挂,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情绪,又一个电话进来。
姐,午饭来你这儿吃,下午还要去省城,事太多,只能麻烦你了。妹妹语气匆忙,旁边还有小外甥的叫喊。
我说,好吧,好吧,反正爸爸也要来。可以确定,我回话时,语气冰冷,她应该可以想象我紧皱的眉头。
放下电话,眼前堆叠如山的作业,再也无心去看了,那些约写的稿子,那些时时涌现的写无数个短篇和长篇的灵感,那些来不及付诸实践的写作计划,以及对想要有的高度的仰视与攀爬,滚蛋吧!什么理想,什么为自己活到十二万分的精彩,什么从书中得到宁静与平和,什么写作令人获得释放,都滚得远远的,我已经没有理由为自己活着,我他妈的为什么就活得这样憋屈?为什么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着,就不能痛痛快快地自己活一场?!我阴云密布地坐在简陋的,乱糟糟的办公桌前,前所未有地委屈,前所未有地厌世,黑色的、黄色的,混浊不堪的气流像龙卷风一样把我团团围住,三十几年来,我所受到的所有委屈,苦难,我所经历的类似于蚍蜉撼大树般不自量力的挣扎,我被别人称道的伪装的坚强,以及种种贤慧,循规蹈矩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足以将人淹没的种种碎屑,齐齐席卷而至,我的疲累、辛苦、无奈、悲愤,我为了尊严体面地生活而付出的努力,我时常上演着幸福实则充斥着怀疑的婚姻,我这个一时兴起而怀上并养大到今天淘气无比的孩子,全部积于一处,使我在这个漩涡的中心越转越快,有一刻,我觉得自己要爆炸了!
电话铃再度响起。父亲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奔出校门,看到几个月不见的父亲,面如土色,浮肿,头发灰白,眼神混浊,诗人的意气风发完全没有了,剩下的,全是颓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晌午的太阳明亮刺眼,长了泡的皮肤要炸开一样痛。我强忍住种种难受,与他并肩走在大街上。红灯,绿灯,车来,车往,他根本不看,他只是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病,毫无目的地跟我穿过这座城市,仿佛世界只剩下我们父女俩。他说话时,总是咳,喉管里总像有痰,却不吐出来,不上不下,堵着他顺利地讲完每句话,听得我恨不得代他咳,代他吐,我本来就紧绷的脸无法在这样的声音里放松下来。
那个,钦儿与你联系么?父亲在咳嗽平息的间歇怯怯地问。
终于还是忍不住提起他,我的弟弟。这是每次相见必修的功课,不管他是身体康泰还是命在旦夕,他的儿子是他永远的牵挂,尽管我无数次提出抗议。他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人生,我不愿意参与他的成功与失败。父亲总是长叹,他终究与你一母同胞,你有能力,应该帮他,何况他是一个正宗名牌大学毕业的,只是运气不佳而已,你该关心他。
我大声说,你知不知道这许多年我又是怎样过来的,为了他我经历了多少本不该我去经历的酸楚?他不是我的儿子,爸爸!
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我这么愤懑的喊叫,父亲噤声了,低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小孩。
我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所有人的午餐。父亲坐在客厅里抽烟,一边抽,一边咳,那声音,像极了不规则的鼓点,敲击着我的每根神经,一下下地发痛,这痛感很快传到了小腹。不多久,一阵盖过一阵的痛逼出我满头大汗。我跑进厕所,尿是红色的,里面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血!接着,痛感一波接着一波,让人有晕眩的感觉。
我只好不停地跑厕所,父亲见我的情形,不知所措。我没有叫疼,不敢叫,下午还要上班,要带他去检查呢,我不能就这么屈服于这突如其来的病!记起去年秋天,情况没这么急,也没这么厉害,好像药还剩了些,先将就着吃点。
就这么扛着,我一边频繁地开厕所门,一边做饭,居然也把六七个菜做好了。孩子他爸爸,妹妹妹夫,也都在我做好饭后如期而至。他们吃饭,我只能坐一旁冒汗。药物缓解了一下疼痛,但小腹的坠痛感依然强烈,尿里的血块一点儿也没少,我得去医院看看。
可父亲怎么办呢?那我先忍着吧。
下午,带父亲去医院挂号检查,三个小时,我至少上了二十次厕所。父亲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轻声地说,这可怎么办?又说,你这是太累了,又说,你要注意身体啊!我一句话都不想回他,我无法让他懂得,每一个人都只知道自己的那一份,不会想到叠加起来对我而言是什么。我的思绪开始全部集中到下腹,对琐碎生活的全部恨意,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除了希望不要再疼,我无法再想其它。
胡乱吃一把药,躺床上休息。我得想想这病为什么来得这样急,我得确知它并不是防碍我活下去的绝症。于娟形容三十二岁的自己是“雄视天空的鹰隼”,这个比喻曾深深触动我,我也想啊,但我飞不起来。
在将近一个月手忙脚乱后,因为疼痛,这个晚上我获得了短暂的休息——躺着,闭目养神,虽然天阴阴的,有点闷,欲雨未雨,一点也没有我想要的满地斑斓容,。我想起了二十岁那年的第一次尿血。
大学刚毕业,因为没有回家乡去工作,我辗转于省城某报社,在一个清晨毅然决然地回来,开始自己创业。那天晚上我熬了一桶浆糊,用毛笔写了二十几张大红纸,趁着夜色出去贴广告(如今这些都已成为城市的牛皮癣),皓月朗照,每一个有空地的墙面,刚去刷两把,就有人过来,说,走走,快走,这里不许贴。语气里写满嫌恶,仿佛我就是那种无缝不叮的苍蝇。我只能陪着笑说,您看,这么多人都贴了,您就给个机会,等我贴好,您想撕就撕吧!说这话时我几乎是点头哈腰了,多么令人恶心的自己!
回到家,接到父亲的通知,弟弟已经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可是家里根本没有学费,我得想办法。我能做什么?我肩膀尚稚,他凭什么相信我能够扛起?他是要逼我卖掉自己吗?年来种种一一浮现,各种情绪山崩海啸而至,整整一晚翻江倒海,不能平息。第二天清晨,我腹部隐痛,尿呈红色,偶有血块。因为年轻,我扛着,继续我紧锣密鼓的创业,以期保证弟弟开学之前的学费能够有着落。三天过去,病自然痊愈,此后自然也没把它当回事。
没想到事隔十五年,那种疼痛会以成倍的力量一路奔涌过来。
十五年,我经历了多少?爸爸,你知道吗?除了把自己卖掉,能做的我都做了!黑暗中,我的心呐喊着,如果我的血管里真的是流的他的血,他为什么竟然丝毫感受不到我的痛?此时,我感觉浑身上下都要胀开,时时处处皆不通畅。
身处黑暗之中,我必须为自己寻到出口的光亮,我何尝没有为此做出努力?当我的老师告诉我有一个学习四十天的机会时,我毫不犹豫一把抓住它,就像溺水之人抓到救命的浮木。文学并非可以学来,但可以有四十天的光阴散漫不羁,这对于从未停下来审视过自己的人来说,实在非常必要。在去之前的几个月里,我无数次想象自己抱着书本重回学生时代,在离开“学生”这个身份多年以后再坐在座位上聆听师者之诲,该是一番怎样离奇而又纷繁的情景?!
然而,事实上,我一脚踏进文学院的大门,便开始了长达40天的逃离之旅。报名时,老师,同学,都那么热情,我看着他们,不能明白他们的热情从何而来;寻找寝室后,洁白的床单和纯木色的床也唤不起我入住的兴趣;第一天晚上的自我介绍使我十分尴尬,因为我从来羞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起自己;每天黄昏时走过宽阔冷清的马路去市府的食堂令我孤独;听各路有成就的作家评论家们的研讨会令我坐立不安。离开了琐碎平常的我,新的轻快的生活,令我无法承受。
于是,有假日时,我急急地往回奔。我奔回到被我厌弃的工作之所,一群孩子跑来告诉我自我离开后他们的种种不适应,他们想我了。那原本令人厌倦的大堆作业,看上去,每一本都充满了温暖而熟悉的气息!而我的儿子,那个淘气得令人头晕的男孩,则扑了我个满怀!对我永远充满怀疑的他,眼神依然冷冷,说,那里既然是你向往的地方,又还回来什么?可是我竟然不再似往日一般排斥,而听到了他的在乎,和对于我回家的欢喜。
我忝着脸皮对他说,很明显,我已经没法离开你。他笑了,抱紧我。
随着学习生活的深入,新的一切铺展开来,我发现,一旦我开始融入这个志同道合者的群体,离开时竟有不舍,而回到日常生活的常态,我也能欣然忘却那种在云端的生活。那时我才明白,我已经成为惯性的奴隶,不可救药!事实上,在旧经验与新经验的对抗中,我摇摆不定,回望来时之路,我的种种不如意,难道不正是我自己混沌不明的结果?我一直以为生命的投注是消耗在正在做的事上,其实,它恰恰是消耗在从此处通往彼处,不断奔跑,逃离,回归,再逃离的途中。娜拉出走之后?突破现实生活,向上,向下?
秋暮的某一个下午,天渐渐冷下来。再次回到琐碎日常中又无所适从的我,忽然感到刻骨铭心的绝望。腹痛如天边的雷声,闷闷地滚了很久,然后,迅猛而准确地袭击了我。我又尿血了。
这次,我再不能不了了之。
我躺在了B超机前,让医生给我看我的肾。
冰凉润滑的粘液在B超手柄的滚动下布满了我的两腰。我屏住呼吸,深感害怕,亲人痛哭流涕的场面在我脑海里反复排演。检查过程显得无比漫长。
漂亮的双肾。医生说,如此漂亮的双肾,真是难得一见啊!你很健康,可是,情绪这个东西,会在身体内窜,一不小心,它就能彻底毁了你!
一瞬间,我的眼里有了湿热的东西。这东西憋得太久太久了,此时它如同腹痛一样毫无征兆地一涌而上。自从长大离开家乡,把我的触角伸向这个拥挤的世界,我在各种经验里奔突,从乡村到城市,我既不能留住乡村的安静与纯朴,也走不进城市的喧嚣与繁华,我无法触及生活真实的核心,因此,也无法与一切爱我和不爱我的人握手成好。无论什么都在我的对立面,不,我站在无论什么的对立面,我所爱和不爱的一切均化作了一支支利箭,毫不留情地射向我,使我原本健康的身体,承受着突如其来的痛楚,逃无可逃。
大概,哪一天,我能与这世界把酒言欢,哪一天,这奇怪的疼痛才不再袭击我?在那冰冷的台子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无法描述的安全。我看到生活这副五彩斑斓的油画,在我眼前铺展长卷。我看到隐藏在油彩下的底子,素笔勾勒,一笔一画,均用力到十分,我看到浮在上面的艳丽油彩,随意点染,不成体系,没成想,退几步,竟成就了完整。
于是胡乱在脸上抹一把,下B超台,笑着走出医院。暮春的阳光温热明净,空气中弥满香樟花的味道。
湘江原创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