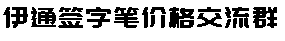文 | 褚笑
注:部分图片文字来源于互联网,版权归作者所有
“泥人张、刷子李……,他们都是行业内数一的人物,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个十万八千里。”
——冯骥才《俗世奇人》
“一技在手,吃穿不愁。”这是一句老话。对于手艺人来说,手艺是一项职业,更是一生的事业和骄傲。
手艺人是渐渐消失的一个群体。然而,在今天的香港,依旧有手艺人以匠人精神捍卫着自己的骄傲。也保留着这方土地的文化印记。他们修补的不仅是一件件平凡的小物,更是人们珍贵的回忆。
初夏多雨,岭南尤然。
身处岭南的香港人上下班路上遇到小雨,就随手买把便宜伞,用后即弃;暴风雨袭来,伞被吹得破烂,人们随手丢在路边,再换把新伞。
这些或旧或坏的伞,大部分人并不在意。但深水埗“新艺城雨伞店”的老师傅却把它们当成宝贝。他说,自己修补的不仅是伞,更是一群人的记忆。
深水埗“新艺城雨伞店”
走进这间三四平米的小铺,映入眼帘的是花花绿绿的伞。长柄伞套着包装齐齐挂在梁上,把店铺的墙壁遮挡了个严实;各种花纹的短柄伞,根据功能分成不同种类,躺在不同的纸盒里。写着店名的牌匾围着红布,挂在店铺的正上方。
店铺里摆满各样雨伞
老板邱耀威是这间老店的第五代传人,深水埗的近邻都亲切地称呼他“威哥”。这家“新艺城雨伞店”原本和小型制伞作坊一起开在广州,后来为逃避战乱搬迁到香港。
威哥接手后,沿用了老一辈的店名,把店一直开到今天。因为从小学习了一手制伞的好技术,在卖伞的同时,威哥也时常帮街坊邻居修补坏伞,时间长了,修伞修出了名声,反而成了这个店的“招牌”。
“新艺城雨伞店”老板邱耀威
威哥将窝钉钳、独牙钳等修伞工具都摆在伸手能够到的地方,方便随时“开工”。他对修伞的手艺有着自己的坚持,伞的间隙框架,都要一一衡量。
他坚持用针线修补伞骨,担心铁线划伤客人的手;在修伞材料的选择上,也“挑剔”地只选择铝片硬度适中的咖啡罐。
威哥细致地修复伞骨
“现在大家修伞,不是为了省钱。修一把伞的钱,都能再买把新的。我修伞,是想大家环保一点,也帮大家保留回忆,所以能修得好一点,就尽心尽力啦。”年过六旬的威哥谈起他几十年来修伞的故事,眉眼间充满了笑意。
“有儿子拿来过世母亲留下的伞,有失恋男生想修复前女友留下的伞,也有奶奶想修好孙子在迪斯尼乐园买给自己的伞,这些已经破旧却充满回忆的伞,在我这里也都是宝贝。”
送修的伞
“我给一对八十几岁的夫妻修过伞。起初我看他们拿来的伞又旧又破,怕是修不好,就劝他们别修了,再买一把。但老两口坚持要我修修试试。一问才知,这把伞是两位老人家年轻时的定情信物,再怎么坏也舍不得丢,希望找我修回原来的模样。”
威哥满脸花白胡子,面带笑容
今日的香港,如威哥般修伞的手艺人已经寥寥无几,跟他同辈的师傅大部分早已“金盆洗手”,享受晚年。而威哥却每年加班修伞400天,每把只收50元,收入并不高,但劳累而快乐着。
“很多伞都是有故事的,不希望有人想要修补回忆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做到的工匠。”
钟楼上空的滴答声缓缓飘远,一点一滴记录着时间的蔓延。斗转星移,四季变迁,日复一日的滴答声中,总有位匠人与钟表作伴。
九龙城侯王道利成表行的吴拾,已经在此经营近六十载。小小楼梯铺,藏着年近百岁的古董手表,藏着各式绝版的零件,更藏着吴伯和它们的半生缘。
开在楼梯底的小铺已和吴伯作伴半生有余
五十年代的香港,还未设有各大品牌手表的维修部,人们用坏了或没电的表,都拿到楼梯底的小店铺维修。吴伯的父亲是位钟表匠,身为家中第十个男孩的吴伯学艺后,在1959年自立门户,从此扎根九龙城侯王道地下楼梯底。
首任业主把与楼梯底相连的地铺卖掉时,把楼梯底留给了年仅21岁的吴伯,并嘱咐他好好做,而吴伯这一做,便是半个多世纪。
如今,即使年近九十,满头白发的吴伯还是缩着肩,日日把“和店铺年纪一样大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摆上,在二、三十尺的小铺里修理古董表。吴伯说,这么多年了,看店修表已经成了他的“心瘾”。
吴伯和他的小店
“修理钟表这种事和开车差不多,做得多了,自然就能掌握个中技巧。我买来坏手表修理,弄断后再焊接,把齿轮折断又重组,就这样慢慢学会修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吴伯因为高超的修理技术和实惠的价格闻名,常有喜爱古董表的艺人慕名来帮衬,周润发、钟楚红、吴镇宇及郑伊健都是吴伯的常客,发哥还曾邀请吴伯拍摄香港特色宣传片。
发哥送给吴伯的照片
吴伯透露,曾有已经移民加拿大的客人专门把手表拿回香港找他修理,亦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有些客人,拿着平凡的老式钟表,走遍中环尖沙咀的大钟表行,都找不到人维修,但吴伯也照单全收:“这表不值钱,谁要给你修啊。但我知道旧物不只是旧物,还有纪念价值。我的柜子里还收藏着几只这样的表,这个不行拆那个,总能拆到合适零件,一定修得了。”
吴伯柜底收藏的各式手表零件
吴伯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救芯的技术。
谈起救芯,吴伯眉飞色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生产的钟表,很多都还没有避震功能。这种“棺材仔”(第一代自动劳力士表,因表底凸起形似棺材而得名)一旦摔到地上,机芯摔断了,就需要种车芯。”所谓种车芯,就是重新再造一条细如丝的芯将表驳回,误差不得多于0.05毫米。
只不过由于年岁渐长,吴伯眼力大减,做工时间变长,好在客人们并不介意,“单据不收,价钱任开”,他们对吴伯的技术有足够的信心。
吴伯修复手表
最近吴伯收到屋宇署来信,说他的小店违反建筑物条例,需要在短时间内搬迁。当被问及是否喜欢九龙城,吴伯这样回答:“不喜欢都不行啦,在这里一世了。我现在老了,没得做的话,就要拿公援了,希望政府能让我捱完这一生……”
随着电子书的流行,人们手里捧着的书本报纸,逐渐被一块小小的屏幕取代,实体书本慢慢远离人们的生活。
在碎片化阅读流行的年代,李瑞云却选择了与实体书为友。
2008年,她在湾仔开起了二手英文书店“书阁”,将旧书一本本打理、清洁和修补过后,才放上书架。
为了修复多年前买下的旧书,她更是不远万里,奔赴英国学习古书修复。时至今日,书店已结业,但她仍坚持修复古书。
“书医生”李瑞云
瑞云与修书结缘,最初只是为了修补自己收藏的旧书。她从小爱书,在旧书摊和文具店中长大,省下的零用钱都用来买书。
工作后,她时常出差在外,也不忘造访世界各地的书店和地摊,见到她小时候喜欢的小说的古董版,不管多烂也要买回来收藏。
修复书本
“我工资不高,买的书十五便士一本,可想而知有多旧多烂吧?”
后来,李瑞云在金融海啸前后被裁员,就决定自己开书店,也开始找人替她修书。但三次找人修补旧书被骗后,她终于下定决心,自己学习这门技术。
求学经历并非一帆风顺。起初,她所拜的导师技术不精且不愿倾心教授;几经辗转,她又认识了英国古书修复专家Flora Ginn,但此人已经不再收徒,她有些心灰意冷。
所幸的是,通过长时间的电邮交流,她的诚意打动了专家,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拜师机会。为了学修书,她只身前往英国学习。除了在伦敦大学学习古书修复课程,她的师父也带她到师公的工作室观摩,教授实战知识。
学习完毕,李瑞云回到香港开始实践。
使用修复纸把破掉的部分补回
修复古书的原则是修复如旧。每一次要修书,李瑞云都会在动手前研究书籍的出版年份、装订方法。遇到不注明出版年份的书籍,她就从纸质或者出版社推断,然后再进行除酸、修复等后续步骤。
李瑞云坦言,修补一本古书并非易事:“我的老师,修过一本约有三百年历史的书,那书掉页、破烂,最大问题是有几页不见了。于是她到大英博物馆找同一个版本的书,把缺了的几页影印,然后重新为那些缺页制版,用相同的印刷方式、字体、颜色,再用古董纸或相近的仿古纸,补回那几页。”
慢工出细活,将一本古书修复好,往往需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
修补古书的工具
在欧洲,古书修复是一门历史悠久的技艺,至今仍然有供有求,但在香港却备受冷落。香港阅读文化不及西方国家,专门收藏古书的人很少,古书修复的市场很小。
“书烂了就不要,平均来说,我一个月也未必收到一本”。除此之外,做古书修复投资很大。专业工具材料需求量大,香港不容易找得到;找得到也要地方收藏,修复时占用的空间很多,“用来做生意、挣钱,基本上很难,完全只能当是兴趣”。
尽管如此,李瑞云仍坚持着,她享受成功修复一本书给她带来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并不仅仅因为自己能够将学来的技术付诸实践,更因为她的努力使爱得到了传承。“
“修书其实是在保存历史,有些人对书有感情,修复旧书除了可以令生病的书重回健康状态,更令它们的寿命比我、比书的主人更长——蕴藏书中的那份爱与尊重能得以继续传下去。”
孩提时代的我们在外玩耍,公园草地摸爬滚打,铁丝网下一展身手。出门还是崭新的衣裳,回来时已“满目疮痍”。每到这时,家里老人都会支起缝纫机,嘎登嘎登,一针一线将衣服补成完好的模样。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人们遇到破旧的衣服,多数都会直接扔掉,不再左补右补。但有家李湛记老字号,却一直经营着织补这门手艺。
“李湛记织补”藏在小巷里
“李湛记织补”位于西营盘东边街的后巷里。小巷里头空气不太流通,店铺顶上也没有瓦片挡头,储物架上摆满了工具和材料,匠人窝在里面做工。
今年82岁的李炳康,是李湛记织补的店主,他16岁入行,在东边街的窄巷已经度过60多个年头。16岁那年,李师傅的父亲发生意外过世,为了赚钱养活母亲及6个兄弟姐妹,他不得不放弃做电器学徒的梦想,继承父亲的衣钵,以父亲李湛为名的店铺也延续了下来。
“李湛记织补”老板李炳康
做织补做了一辈子,李师傅的技术可谓娴熟,凭他一双巧手,大部分破旧衣裳经他织补后,都可回复九成原貌,就连玻璃丝袜也能修补如新。
谈起修补丝袜,李师傅颇有话说:“五六十年代,丝袜动辄两三百元一双,是当时的“潮物”。但丝袜易坏,又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买一对新的,所以那时候好多人找我补丝袜。”
丝袜线细,修补的时候需要非常集中,那时的李师傅常常熬夜帮客人修补丝袜,但后来丝袜越来越便宜,李师傅的生意也逐渐冷清了下来。
修补丝袜的手艺鲜有人知
随着经济的发展,织补业逐渐没落,李师傅的生意数量相比从前减少了许多,但却仍不乏忠实粉丝。近至港九新界,远至澳美欧洲,都有顾客慕名来帮衬李师傅的,更有客人专程赶到东边街与李师傅拍照,足可见人们对于李师傅的信任和爱戴。
被问及入行多年的秘技,李师傅却十分谦虚,“哪有什么技巧啊,就是细心做好事情啦,慢工出细活嘛。”
细心做足就是技巧
“有些衣服很古老了,我告诉他们别补啦,客人说不补不行啊,这是过世的母亲留下的,补好了还要传给下一代。”
这其中也不乏浪漫的爱情故事。李师傅也深知,客人想留住的并不只是一件衣服,能尽一己之力,他觉得很荣幸。“有的人会拿有纪念价值的衣服来给我补,这份信任我很珍重,能帮到客人补好衣服,都很满足。”
李师傅的铺头不乏外国友人光顾
如今,年过80的李师傅眼神依然犀利,能看到微小的针口;他的双手也够定力,穿针引线完全不会手抖,修补一个个破洞。纵然已是耄耋之年,家中儿孙满堂,本可以退休,李炳康却不愿离开他的小铺,连新年多放几天假都觉得无趣。
“儿女好多年前就劝我退休,但我觉得没有事情做就好无聊,所以能做一年就是一年啦,有点寄托嘛。”虽然不舍这份工,但李氏夫妇并不希望子女再继承这份家业。“这行太辛苦,做其他行业发展会更好,做这些干嘛,淘汰啦……”
曾有记者问一对老夫妇:
“你们是怎样维持一段关系足足65年?”
老妇这样答:
“在我们诞生的年代,当有东西坏了,我们选择修理它,不是舍弃它。”
情归于器,器自有情,念旧实是念情。
若有人想修补回专属的回忆,而能帮他们的人还在这里,又有什么不好呢?
时节、故事、情怀。
从古至今,文化从未失联。
愿文化富有温度,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