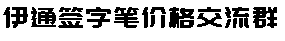
2022-07-05 15:26:30
他冲过去一把揪住赵芳草的长发,拖着她往墙上撞。小武的手下意识地抱住头,那天他才被人拽去撞墙。赵芳草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抓住吕光明的手就啃,像啃玉米棒。吕光明发出痛苦的呻吟,只好撒手...
门外
01
小武到城里找爹,把当爹的吓了一大跳。
深更半夜的,出租屋的大门被拍得又急又沉,吕光明心里一格登,血全涌到脑门心,双手松开了,怀里的莫慧兰如鱼儿般滑进了被子里,小声问,半夜三更的,谁呀?吕光明嘘了一下说,肯定是我乡下二舅跑来借钱。莫慧兰掐小嗓音说,那你就借一点呗。吕光明的胸腔里一定是发出了咆哮,只是莫慧兰听不到,她听到的是一声含糊的冷笑,借过了,再借,咱们还要不要买房子?还要不要生娃娃?莫慧兰的眼睛亮起来,切,少给我灌酒,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她离?吕光明说快了。这时拍门声又震荡开来,一下一下,相当的撼人。吕光明跳下床,摸出卧室,穿过客厅,趴在门后对着猫眼往外瞄。楼道里光线昏暗不见人影。
跟在吕光明后边的莫慧兰用屁股顶开吕光明,将脑袋凑上去,嘴里嘀咕着,什么呀,是个屁小孩嘛。吕光明扳开莫慧兰一瞅,马上乐出声来,我儿子,我儿子……他啪地打开厅里的灯,拉开门,把蓬头垢面、摇摇晃晃的小武一把拖了进来。小武的目光先跳到父亲脸上,马上又跳到后面去。吕光明跟着回过头,莫慧兰正双手护胸,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戳在地上的一截木桩白得晃眼。
小武瞪大着眼睛问,爹,她是谁?吕光明拘谨地笑,朋友,非常好的朋友。眼尾才浮起两撮皱纹,又迅速地消失了。莫慧兰白了吕光明一眼,偏着脑袋作思考状,眼珠子滴溜溜地转,没错。我家停水了,到这边来借冲个凉,这不,正想走呢。
小武用舌尖舔了舔干燥的上唇,不好意思地笑,这城里的女人说话吧,真好玩,嘴里像含了水,真担心它会滴下来。
吕光明镇定了下来,问儿子怎么跑出来。小武没吭气,目光跟着莫慧兰跑,在她拐进卧室时才弹了回来。他揉了揉眼窝说,娘她、她……吕光明想,这小子准又干了坏事,要不怎么会被逐出家门?就忿然作色,好啦好啦,你活该!小武知道他误会了,气急败坏地叫起来,不是的,这回不关我的事。吕光明往卧室那边望了一眼,用力捏了捏儿子的肩膀,好啦好啦,有话呆会儿再说。小武很不服气地哼了一声,刚把嘴巴张大,那个女人就出来了。她把小武的脑瓜当皮球拍了拍,说了一句长得真像你爹,就把嘴巴凑到吕光明耳边。小武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看到父亲偏着头,眉毛一跳一跳的,很难受的样子。
02
人都走了,吕光明还不停地眨巴着眼,就像她还留在眼眶里头,撑得眼皮子一紧一松的。小武喊了几声爹,才把他喊醒。他粗暴地推开儿子,光着脚咚咚地跑下楼去。
小武跑到阳台,踮起脚尖往下望。父亲已经追上那个衣不蔽体的“好朋友”,拦在她的前头,嘴巴不停地说着什么,两只手上下翻飞,如耍两把短刃,把那个女人吓得连连后退,生怕被削掉鼻子挖掉眼睛似的。
吕光明回到家,小武早就趴在床上打起呼噜了。他摇了摇头,无声地叹息,这赵芳草也太狠心了,哪有这么管教孩子的。又转念一想,是不是她故意给自己制造点麻烦?
不过说实话,小武也的确难管,不认真念书也就算了,还到处惹是生非。邻居的猫狗死了,或者瓜秧子被连根拔起,第一个就怀疑他。这不能怪赵芳草,,毫不留情。春节回家,吕光明撩开儿子的衣服,身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好肉,触目惊心。他心里到底还是明白,在儿子这么多的伤痕里,至少有一半替他挨的。吕光明和赵芳草原本感情不错,自从他外出打工后,两人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偶尔通个电话,说不上几句还吵起来。赵芳草嫌吕光明给的安家费少,不如回家带孩子,由她出去算了。吕光明就嚷起来,喊我出去的是你,喊我回来也是你,你老公就这点出息,有本事你找个更好的。赵芳草说别以为你是个香饽饽,当初要不是你三求四跪,老娘我能嫁给你这个歪瓜裂枣?话说到这份上,很伤人了。
吕光明的确是被赵芳草逼出去的。看到村里人到深圳、东莞打了几年工,回来后就盖起大瓦房,赵芳草再也坐不住了,不停地撺掇老公,这年头撑死胆大吓死胆小的,你吕光明哪点比别人差,凭什么要埋没在这穷乡僻壤?吕光明担心闯不出个名堂,回来不好交差,就迟迟疑疑地说,怕不行吧?赵芳草的声音近乎吼,男人不能说不行!不试怎么知道?
03
那年元宵后的一个黄昏,赵芳草带着儿子,把吕光明送到村口的国道旁拦车。北风漫卷,树木抖响,赵芳草替吕光明翻好衣领,又捋平他后背的褶皱,那庄严肃穆的神情让人想起“岳母刺字”的那段说书。她用目光代替了金簪,在老公脸上刺下“精忠报家”四个字,深入灵魂,感人至深。她说光明,你放心好了,家里的一切有我。吕光明在喉咙头呜咽了一声,又感动又心酸,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芳草,丑话说在前,是你叫我去的,好好坏坏可就由不得我了。看着吕光明上了车,赵芳草这才忍不住地抽泣起来,断断续续的哭声被风传出很远。小武拽了拽赵芳草的衣角说,娘,别哭了,爹是去发财,又不是去奔丧。
吕光明到城里打工,每年回家一趟,一般是在春节,差不多呆了一礼拜,又打点行李匆匆上路。在小武眼里,家成了父亲的旅店。在放假的日子里,吕光明每天都睡得很晚,不是跟堂兄堂弟喝酒,就是拉一帮狐朋狗友搓麻将。儿子有时站在旁边,吕光明就会端起酒杯让他尝一口,然后看着他吐出舌头得意地笑。要是打麻将,吕光明就会赶他,大半夜了,赶紧回去睡觉。小武白了父亲一眼,顶他,大半夜你还玩?都输了多少了。吕光明倏地站起来,装出要揍他的样子。小武知道父亲是在吓唬他,从小到大,他没动过他一根指头。父亲对他可好了,每次把电话打到附近的杂货铺,总要点名让他去接。接完了,问要不要让娘也来听听?通常父亲都说不用,你告诉她就行。
在外出打工的第四个春节,吕光明驾着小车衣锦还乡。那车就泊在河堤的一大蓬竹子底下,识货的人说那是辆桑塔纳。天刚蒙蒙亮,小武就站在车旁,逢人便说,我爹当老总了,这车是他的。大家开始并不相信,还拿他寻开心,他就气呼呼地跑回家,过了一会儿,吕光明就咬着牙签挺着肚子、器宇轩昂地走来,一把拽开车门,插上钥匙,轻轻一拧,那车子就像妖怪见到孙大圣浑身发起抖来。村里人都说,吕光明发了,赵芳草母子不用愁了,等着哪天进城享福吧。赵芳草听后只是笑,笑得比哭还难看,吕光明哪像个老总?安家费一个子不多给,还拖拖拉拉的,一副要赖账的样子。赵芳草试探过他,说不如把小武接到城里去上学,那里的教学质量肯定高些。吕光明睁眼说瞎话,什么城里的学校不收外地生啦,什么民工学校都是些垃圾啦……听着听着,赵芳草心里就犯嘀咕,敢情这吕光明已经当了陈世美,在城里又了安一头家?
04
就在去年,吕光明生日的前晚,赵芳草决定上城去,一是犒劳一下老公,给他一个惊喜;二是修复一下两人的感情,顺便摸摸底,他的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春节时,她多留个心眼,偷偷地配了老公的钥匙。从村里到城里,坐车只需五个钟头,结果赶上修路,大塞车,折腾到吕光明的出租房已是第二天清早。好在赵芳草这回不晕车,还睡着了,不仅睡着,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潜入老公的出租屋,光溜溜地钻进他的暖烘烘的被窝里……醒来后,老公那又惊又喜的表情仍历历在目。她的脸一下红了,居然有点想。到了出租屋,她竭力抑制住内心的兴奋,悄无声息地开门,摸进卧室,才把衣服脱了一半,不动了,屏息静听,床上传来了两个人的呼吸声,粗中有细,此起彼伏。赵芳草果断地掀开被子,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睡在吕光明身边的那个女人头发蓬松、面色红润,肌肤紧滑,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她镇定地围上纹胸,反手扣上,再把两条雪白的长腿挪到床沿,垂下脚丫寻找那双原本属于赵芳草的拖鞋。望着那一波三折、火辣辣的身材,赵芳草竟忘了冲上去抓她个“满脸花”,相反还自惭形秽。待外面的门哐地关上,她才像挨了巴掌似地醒过来,扑向那个负心汉。吕光明边往后退边嘿嘿地笑,闹着玩的,你看你,还当真哪?
闹着玩?离!
赵芳草的眼里聚起灼人的光亮,光亮的深处是无尽的绝望。
吕光明还在笑,但那种笑已经苍白无力。他知道赵芳草不会离,但也不会让他好过。
从城里回来后,赵芳草一个劲儿地掉肉,双颊凹得更厉害,眼睛显得格外的大,大得空洞,大得荒凉,大得冷漠,好像世间万物转瞬即逝,与她毫无关联。她的脾气比以前更大,动辄就打小武,就像她的不幸全是儿子一手造成的。
人们隐约意识到,吕光明把赵芳草变成了一枚炸弹,随时都会爆炸伤及无辜。
小武跑到城里来是想告诉父亲,母亲跟他的班主任蒋老师好上了。
小武升上三年级,班主任换成了蒋老师。蒋老师四十开外,长得又矮又胖,秃顶,留长的头发绕额盘成一圈,架一副黑边眼镜。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光棍汉,据说年轻时谈了个女朋友,因为家里不同意,那姑娘一时想不开喝“敌敌畏”走了。也有人坚持说那姑娘死时还怀了蒋老师的骨肉,蒋老师就发誓终生不娶了。
05
小武三天两头在学校捣乱,赵芳草也就三天两头地往蒋老师那边跑。当着蒋老师的面,赵芳草毫不客气,剥下鞋子就往儿子身上抽。同学们经常看见小武像条疯狗满操场乱蹿,赵芳草举着鞋子在后面穷追猛打,要是进入“射程”之内,她就会果断出手,把鞋子变成飞刀直奔小武的脊梁骨或后脑勺。蒋老师总是落在最后面,他人胖腿短,跑起来相当费劲,可他并不泄气,勾着头不屈不挠地跑,嘴里还不停地劝,小武她娘,孩子要慢慢教,你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赵芳草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放慢,她气喘吁吁地答,你以为他会怕?这样他都不怕!蒋老师也跟着喘起来,声音变得断断续续,你都、知道他不怕,这说明、教育方法有问题……赵芳草就耍起横来,怎么怪起我来?我把孩子交给你们,是你们没管教好。蒋老师说,唉唷,这样说话太累人了……我不是在教吗?你能不能停下来说。赵芳草望了望儿子逐渐变小的身影,又回头望了望满头大汗的蒋老师,只好收住脚步。
唉呀妈呀,你看你们都教出个什么来?赵芳草叉着腰,张开嘴,远远望去,像在大口大口地吞咽空气。蒋老师追上前,捞起那绺飘来荡去的长发,慢条斯理地说,这要家校齐抓共管,叫你来,不是要你打孩子,是要跟你商量,一起拿出个好办法。
看着蒋老师的狼狈相,赵芳草有点于心不忍,小武又不是他的孩子,他还这么尽力,再看看吕光明,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说咋管嘛?蒋老师说,要多跟孩子交心,多跟他讲道理。这教育孩子,就好比谈恋爱,要多谈,谈到他的心里去,才能对症下药。靠打?那是王老虎抢亲。赵芳草扑噗地笑开来,她发现自己好久没笑过,脸上像长了层壳,僵僵的舒展不开。
蒋老师和赵芳草从教育孩子入手,不知不觉地扩大谈话范围。在赵芳草眼里,蒋老师的嘴巴真能讲,讲着讲着,自己便成了主角。他谈他的童年,学生时代,还毫不避讳地说起死去的女朋友。他向她保证,他没有和她那个,她的轻生反而让他看得更明白,她是个脆弱且不负责任的人。赵芳草不停地用微笑和点头支持蒋老师,她要让他相信,那些谣传在她眼里只是一堆狗屎。当话题绕回到小武身上时,蒋老师郑重其事地提问,为什么孩子惹事后总是赵芳草来,而不是她的那位?一想到那个挨千刀的,赵芳草的泪水就止不住叭嗒叭嗒地掉。走的时候,蒋老师红着脸对赵芳草说,你长得有点像我的那个女朋友,不过比她更好看,更成熟。
很快,小武在母亲的身上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脸上有了笑容,嘴里还破天荒地跑出歌声来。她“骚”起来了,头发重新烫过,浑身上下焕然一新。往常那些钱,就像长在她身上的毛,拔哪根都喊疼,现在倒好,时装一买就是好几件,桃红柳绿的,一天一换,跟翻日历似的,都开展览会了。她开始热衷于串门,出门前,总要对着镜子眉来眼去,明明是块黄泥巴,偏要捏出个金元宝!一天傍晚,她的前脚才一出门,小武的后脚就跟上去。在影影绰绰的暮色里,小武发现母亲的身材其实还保持得很好,有胸有臀,腰肢扭得像风摆柳。沁凉的风吹在赵芳草身上,又吹到小武身上,他嗅到风里夹着一股好闻的香水味。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过龟背桥,绕进小巷子,转出来,已经到了曲河小学的后门。赵芳草朝四周望了望,钻进去。小武的心马上沉下去,果不出所料,母亲和蒋老师暗地里互相勾结,连手对付自己。今天,他又往班长书包里塞了几条四脚蛇,她不该向老师打他的小报告。小武尾随母亲穿过操场,来到蒋老师的办公室,里面没开灯,门却虚掩着,小武正纳闷,母亲已经侧身闪了进去。小武不敢进,只好躲在窗子底下偷听他们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没有具体内容,只听到蒋老师午休的铁架床发出了一些声响,很重很急,中间还夹杂着两个人的哼哼声。小武忽然明白了,这个明白吓得他失声尖叫起来,屋里登时涌出一阵杂乱的声响。他拔腿就跑,边跑边听到母亲在后面喊他,那声音由强变弱,直至消失在风里。
06
小武知道母亲不会饶过他,就索性跑回家,取出过年的压岁钱,像父亲当初去打工那样,在村口拦了辆路过的长途车。他知道父亲住在哪里,他才寄来过一个复读机,上面有地址。
小武那一觉差不多睡到中午,阳光从窗户爬进来,抚摸着他的屁股蛋。吕光明过来轻轻地摇他,小武,醒醒,爹买了你爱吃的豆浆油条了。小武像只刚出生的猪崽,眼睛勉强撑开一道缝,光亮如水般地溢出。
吕光明把儿子推进洗手间,待他冲完凉,又拿了条大毛巾帮他擦头发。小武躲闪着,一屁股坐在那张折了条腿、靠在墙边的餐桌旁,拿起油条就往嘴里塞。吕光明也坐下来,一脸巴结的神情,慢点,小心噎到。
吃着吃着,吕光明的手停下来了,问儿子,你盯着我看什么?不认识你老子啊?小武把头垂下去,小声地争辩,我盯着你了么?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告母亲的状,吕光明就堵住了他的嘴,小子,昨晚你做了个梦吧?小武茫然地摇头,记不得了。吕光明扯了一截纸巾,帮他揩掉嘴边的油条碴子说,怎么记不得,你梦见爹的房间里多了个女人,对不对呀?小武叫了起来,那不是梦——。吕光明摇了摇头说,怎么不是梦,那人呢?小武左看右看,撅起嘴说,早被我吓跑了。吕光明眉头纠结,脸上的一道新伤痕给他平添了几分杀气。小武明白了,父亲要他把昨晚的事当个屁放掉。果然,吕光明严肃地说,你什么也没看到,你只是做了个梦,懂吗?小武听到嘴里的豆浆咕噜一声,簇拥着母亲的糗事一起咽进了肚子里。
为了安抚儿子,吃完早餐,吕光明把他带到热闹的东门去逛逛。从停车场出来,父子俩绕了一圈,走上步行街。吕光明捋了一下儿子乱糟糟的头发说,长高了,都快到我肩膀了。小武不出声,好奇地打量着从身边经过的男男女女。这时还是上班时间,逛街的人并不多。前面有个大商场,临街的橱窗高大明净,里面摆着些塑料模特儿,都穿着时髦的装束:贴身的背心,宽松的T恤,飘逸的长裙,闪光的晚装……一个个形态各异,花枝招展。小武捏着一盒饮料,吸管含在嘴里慢慢地吮着,眼珠子好久不眨一下。他的影子淡淡地映在玻璃上。吕光明问,漂亮吧?小武没有回答,只是笑。他发现离自己最近的那个模特儿有点像母亲,身材修长,脸上颧骨突出,眼睛凹陷,头发盘在脑后,更巧的是,它的身上穿了一件母亲才新买的衬衫,粉红色,像道霞光一样透亮、明快。
你小子也开始喜欢女人了?吕光明捅了儿子一下嘿嘿地笑。小武用力吮了一下吸管,盒子里发出了呼呼的空响,就松开嘴,指着那个模特儿说,它挺像我娘。吕光明把嘴里的烟夹到手指间,饶有兴趣地问,怎么个像法?小武转过头来,玻璃上留下一圈白雾。他认真地答,人长得像,衣服也像,只不过呢……她呆在城里,我娘却老呆在村里头。吕光明脸上的肌肉就抽搐了一下,腮帮子陷落,烟头嗞嗞地朝后跑了老长一截。他知道,儿子是在怨他,没把他们娘俩接到城里一起生活。吕光明心里一下又没底了,这小子会不会去向他娘告状啊?正想着,手机的彩铃唱起来了: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他把手机摁在耳朵上,听着听着,神色就不对了,从裤兜里掏出张钞票塞到小武的手心里说,爹公司有急事,得马上走,过会儿来接你,就在这橱窗前,别跑开啊。
小武可怜兮兮地望着父亲,手足无措。吕光明跑了几步,又跑回来对他说,别人叫你去哪里,千万别去。小武问,爹,城里有坏人吗?吕光明边退边说,哪里都有坏人。记住了,就在这橱窗前等我。
07
差不多到了下午两点,父亲还没来,小武的腿肚子像钻进去好多虫子,麻酥酥的,肚子也瘪下去,咕咕乱叫。前面不远处有个老头在一辆小推车上煮花生、茶叶蛋和玉米,那喷发出来的香气如一双大手,蛮不讲理地把小武拽过去。站在小推车前,他用力地吸着鼻子,右拳却松开了,那张钞票如一枚沾了露水的枯叶湿漉漉皱巴巴的。他还没想好买点什么,不知道哪来的一只手,呼地一把夺走了钞票。他尖叫一声,对着行人乱推乱撞,可哪还找得到人?他有点不相信,又盯着地面寻了老半天,就像钞票是被风刮走的,最后,只好空着肚子回到商场的橱窗前,有泪珠从眼角慢慢地颠出来。
小武从下午一直等到黄昏,夕阳敛尽光焰,缩成猩红浑圆的一团坠向高楼后面。天还亮着,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一片片如潮水。小商小贩出来摆地摊了,花花绿绿、密密匝匝地一路铺排下去,吆喝声此起彼伏。小武紧紧地盯着人群,好像眼睛一眨,父亲就从身边溜掉。这时那些烧饼、羊肉串的香味,正以压倒一切的姿态朝他奔来,不怀好意地将他推来搡去。他摸了摸肚皮,它都快贴到后脊梁了,两条腿有点像冰棍,先是过分的僵硬,现在又软遢遢的快要融掉。他变得疑神疑鬼的,不停地问自己,父亲是不是来过?找不着他又往别的地方去?为了看得更清楚,他在街边挑了棵树,手脚并用噌噌噌就爬上去,再往下看,到处是晃动的人头,还有从羊肉串小摊飘上来的白烟,那些烟被风吹来吹去,像摆起了迷魂阵。小武瞪大眼睛努力地搜寻,可那些脑瓜就是不老实,转来转去,起起伏伏,把他的眼睛都晃花了。不经意的,一个身影闪进小武的视线,那是个跟他差不多大的瘦男孩,他紧贴着地摊前的一对情侣,偷偷地拉开那个女的的背包。小武从树上跳下来的,奋力扒开人墙,推了那孩子一把。那男孩烫到似地把手缩了回来,瞪着小武,陡然大叫起来,抓小偷,抓小偷,他是小偷。那个女的急忙把背包转到前面去,迅速清点起里面的东西。男的揪住小武不放,你想干什么?小武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我,是他。手一指,才发现那个男孩不见了,只好说,跑啦,他跑啦。女的把拉链拉好,鄙夷地说,贼喊抓贼!见没丢东西,那个男的松开小武的细胳膊,却在他无肉的屁股上狠狠地蹬了一脚,把他蹬了个狗啃屎。小武才爬起来,旁边又闪出条壮汉,揪着他的头往橱窗玻璃上撞,嘭嘭嘭的,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叫你偷,叫你偷……好些人围上来,七嘴八舌指指点点,叫嚷着把“小偷”送进派出所。幸好有个老人替他解围,说算了算了,还是个孩子嘛。小武像一袋垃圾,被扔在了橱窗下面。他筛糠似地发抖,感觉有液体热乎乎地从鼻孔流出,拿手背一抹,竟抹出一片猩红来。更气人的是,那个真正的小偷就明目张胆地站在他面前,歪着嘴,笑得肚皮一颤一颤的。小武剥下鞋子,学着母亲那样奋不顾身地扑过去。那男孩嬉笑着躲到壮汉后面,看着他一手擒住小武的细胳膊,一只手揪住他的头发,把他当陀螺转。小武只觉得头顶裂开似的疼,五脏六腑都快被他甩出去了。他咬住牙不哭,但喉咙头还是忍不住地发出吱吱声,像一只被人踩在脚底下的小耗子。
嘭的一声巨响,小武像把鼻涕,顺着橱窗玻璃粘不住地滑落。不知过了多久,他缓缓地睁开眼来,四周飘忽着,宛若水波一漾一漾,那些嘈杂的声音又一下子涌进他的耳朵里。他支撑着想站起来,可就是站不起来,只能拿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男孩,盯得他脸色都变了。人群渐渐散去,小武听到自己的声音凶残而又高傲,小王八蛋,我爹是个老总,看他回来怎么收拾你,小王八蛋!
08
晚上七八点,忽然起风,黑云锅盖似地扣下来,把步行街的灯火衬得更加鲜明夺目。树叶纷纷扬扬,紧贴着路面和树根,几阵雷声滚过,雨开始白亮亮地下起来。行人抱头鼠窜,小贩横冲直撞,天地间一片迷茫,滔滔不绝的雨水从四面八方涌到街口,载着斑斓的灯火和树叶残花向两边分流。商场的门口挤满了避雨的人,一个个神色黯然,对着雨幕出神。小武像条蛆,一拱一拱地挤到前面,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慢慢的,他觉得头有点晕,站不稳了,只好蹲下去。漂飞的雨丝落在他的脸,冲开了污垢和血迹,滴落在脚底。他低下头,台阶下的一只梨芯立刻跳进了他的眼睛里。它黑乎乎的,有只苍蝇在周围绕来绕去。他咽了下口水,费劲地伸出手,用指甲碰了碰它。苍蝇飞了,他的脸也红了,都想不理它,就有奇香扑鼻,抬眼一看,一只松脆的榨鸡腿在一个小姑娘的手里灿然夺目。他的肚子里又一阵翻江倒海,眼前全是纷纷扬扬的金黄,犹如下起了太阳雨。他顾不了太多,一把夺过梨芯塞到嘴里去,有股酸臭味呛得他涨头涨脑地咳起来,每咳一下,松弛的肚皮就狠狠地拉扯一下,抽筋似的痛。他能感觉到那些没有嚼碎的梨渣硬梆梆地摩擦着食道,沉甸甸的快把胃肠坠破。好在酸臭味很快就消失,喉咙里像长出一只手,将剩下的那点梨芯全抓下去,又伸出来喊要。小武决绝地摇摇头,对着喉咙和肚子说,没有啦,就这么多了。
雨停了,空气变得沁凉如水,步行街的灯光一片片地暗下去,只有小武旁边的橱窗还亮着,那些女人或站或坐,隔着玻璃与他作伴。他感到额头发烫,伤口火辣辣的,手臂重得抬不起来。他下意识地挪了挪,紧靠橱窗,一阵无比清晰的霜寒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切入肌肤,他的背后一下子空了,荒凉了,无依无靠的。夜色沉得压人,黑暗犹如巨口虎视眈眈,他急忙往橱窗望了一眼,那个像母亲的模特儿正亲切、慈爱地注视着他,让他稍稍定下神来。他不断地对自己说,爹很快就会回来,爹很快就会回来……可这样的念叨更像一支催眠曲,有好几回,眼皮都耷拉下去了,又被他顽强地撑起来,他怕睡着了听不到父亲的叫声。为了不让自己睡去,他灵机一动,开始跟橱窗里的“母亲”说话。他说娘,爹很快就来接我了。他又说娘,今天我看见小偷呢,我抓不到他,还叫他给坑了……他说娘,我再也不调皮捣蛋了,回去后一定要好好念书,替你和爹争一口气……他的声音如珠子,闪亮着,弹跳着,滚向远处,有泪水涌起,长出了针尖麦芒,那些橘黄色的灯光从橱窗里漫了出来,流光溢彩,犹如一条缎面被子柔软、温暖地将他拥进怀抱……眼皮不争气地耷拉下去了,他奋力挣扎了一下,想要撑开一线光明,可是黑暗铺天盖地,势不可挡。
吕光明是在凌晨一点多找到小武的,他一瘸一拐地过来,发现儿子蜷缩在橱窗前,紧贴着玻璃的脸罩着一层透明、颤动的泪光,嘴巴张开着,像在诉说什么。吕光明弯腰想把儿子抱起来,却抱不住,手上的肌肉撕裂般地疼痛,只好推了推他。小武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呈现出一张狰狞的脸:血迹斑斑,头发散乱,凹陷的眼眶间也挂了好几绺,眼珠子显得幽深恐怖。他尖叫着拼命往后退,是熟悉的声音把他镇住的,儿子,是爹,别怕,爹这就带你回家。
父子俩互相搀扶着,摇摇欲坠,站在路边招手,有的士打身边过,就是不肯停下来。小武突然想到什么,问,爹,你的车呢?吕光明不好意思地说,爹的车让人偷了。小武想了想又问,爹,你有没报警?吕光明挠了挠后脑勺说,报了。小武又问,那车子什么时候才能找回来?吕光明咧着嘴苦笑,我也不知道。小武说,爹,你肯定是被人打劫了?要不脸上怎么会有血?吕光明用手指轻触了一下,咝地倒吸了口冷气,话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狗日的,出手还挺狠的。小武明白了,爹一定是跟人打架。爹也爱打架,难怪娘不喜欢他。
09
半个小时后,终于有辆蓝牌车愿意送他们回去。到了城中村的路边,司机怎么说也不肯进去,大概是怕遭暗算。父子俩只好下车,化作两团黑影,一大一小,一高一矮,颠簸着往深处走。拐过巷子,出租屋就到了。吕光明正往身上摸钥匙,暗影里就蹦出个人来,把父子俩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是莫慧兰,她生气地说,快把我急死了,门也锁了,打你手机也关机。吕光明拍了拍裤子两侧的口袋,无奈地说,妈的,手机也丢了。上了楼,灯光一照,莫慧兰惊叫起来,吕光明,你、你怎么啦?你儿子也是……
吕光明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儿子,一时语塞,就听到小武替自己回答,我爹被人打劫了。他狠狠地点头附和,没错,我们被打劫了。又推了儿子一下说,快,进里面睡觉去,我和阿姨说会儿话。小武知趣地跑进房间,躺在床上,奇怪,肚子也不饿,睡意也没了。他听到父亲过来把房门拉严,站在厅里跟那个女人说话。
刚开始气氛还很缓和,声音低低的,像是有商有量,慢慢的,两个人的嗓门都大起来。那个女人对父亲说,吕光明,你别把我当傻子了,哼,什么老总?告诉我,你究竟是干什么的?父亲说,你很在乎我干什么吗?那个女人说,我当然在乎了,我可不愿意稀里胡涂地嫁了个地痞流氓或者杀人凶手。父亲说,我告诉过你一万遍,我是财务公司的。那个女人发出一连串的冷笑,就凭你的学历,也能在财务公司混个老总?父亲叹了口气,好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专门替别人追帐的,不过对外,我们都叫财务公司。那个女人笑了起来,笑得肆无忌惮。小武在暗暗给父亲使力,给她一巴掌,看她还笑不笑得出来?那个女人把笑声用力一收,话迸了出来,你说是的不就完了?父亲就像面对客户,认真而耐心地纠正她,我们不是,我们是替别人追帐的。那个女人又笑开来,那还说不是?父亲终于吼起来了,伴有玻璃砸地的脆响,在黑暗中,小武仿佛看见那些玻璃碎屑闪亮地向四面八方迸射,雨点般地撞击着两个人的脚踝,疼痛如针扎。莫慧兰,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是,我是在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懂吗?厅里一阵沉默,空气像凝固了似的。过了一会儿,父亲的声音又悠悠地传来,莫慧兰,你还愿意嫁给我吗?伴随着一阵低低的抽泣声,那个女人开口了,可以,不过有个条件。父亲问,什么条件?那个女人说,就我们俩,要儿子咱们自己生。父亲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没问题,让他跟他娘好了。那个女人又问,你们什么时候离?父亲答得更加干脆,过两天我回去一趟,把事给办了。
两天后的傍晚,吕光明在给赵芳草打过一个漫长的电话后带着小武回了老家。
赵芳草一见儿子就冲上前,拎着他的耳朵往里屋拽,拽到床边,黑着脸小声问,小兔崽子,究竟你跟他说了什么?小武急忙摇头,这一摇,耳朵就有了撕裂般的疼痛,只好不摇,用嘴巴说,我啥也没说,真的。母亲不信,把脸凑得更近,像要把他的五官挤扁压平,你要是没说,那个混蛋会跑回来跟我离婚吗?就算离婚,我也不要你,讨债鬼!她甩开儿子,拍了拍衣服上看不见的灰,气汹汹地走出去。吕光明就站在天井,目光斜斜跟着她一路过来。她咳嗽了一声说,我不想离,是你要离的,条件得由我开。吕光明笑了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开吧,这房子归你了。赵芳草说,这烂房子顶屁用?我要的是钱,不多,给二十万。吕光明像遭鞭子狠抽,浑身震了一下,大叫起来,赵芳草,你真敢开口,别说二十万,就是两万块我也拿不出来。
10
小武从昏暗的里间走出来,倚着门框,眼眶红红地盯着父母,如看一出悲剧。他知道这个家无可挽回地要破裂了,不知道自己最后会跟谁?父亲已经跟那女人说过不要他了,母亲刚刚也说过不要他,但愿那只是一句气话。
赵芳草尖着鼻子冷笑一声,一个搞财务的大老总,拿不出二十万,是不是叫狐狸精给管死了?吕光明的目光软了下去,掏出烟来燃了一根,让烟雾和话一起吐出来,你误会了,我不搞财务。小武发现父亲的脸红了。赵芳草说,你跟我怎么说过的?原来是个骗子!吕光明笑了笑,态度诚恳地说,我不搞财务,但也一样跟钱打交道。我们是追债公司,对外都叫财务公司。这就好比我有两个名字,官名吕光明,乳名牛蛋蛋。赵芳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像终于发现了他脸上的疤痕和手上的绷布,嗓音尖厉起来,听上去有点发颤,这么说你是的啰?吕光明摇了摇头说,我不是,我是替天行道,像《水浒》里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赵芳草扑噗地笑开来,原来还是个大英雄,那就豪气一点,起码给这个数。她的手掌翻了几下。吕光明苦着脸问,五千?赵芳草撇了撇嘴,你想啊,十五万。她瞟了一眼儿子,他正无助地啃着指甲,就骂了一声,小武,别啃指甲。又转过头来对吕光明说,还有,这捣蛋鬼归你,我不能要他,我管不了他。
吕光明一下蹦起来,蹦得老高,不可能,儿子归你,房子也归你,一口价,两万。赵芳草说,做你的大头梦吧,无论如何这孩子你得带走,钱可以少一点,十二万。吕光明说,莫慧兰她能生,她不要孩子。赵芳草扯开嗓门,想用更大声音来压住他,人家老蒋还是条光棍汉呢。
吕光明愣了一下,沉下脸来问,谁是老蒋?小武按捺不住地冲上前,手指在父母之间来来回回地比划,爹,你替我作证,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娘和蒋老师的事?
赵芳草马上反应过来,呼地给了小武一嘴巴,闭上你的鸟嘴!
小武只觉得眼冒金星,脸上像放了一把火。他摸了摸脸,有五根指印立了起来,比自己的手大,捂也捂不住。
吕光明仿佛多了一件制胜法宝,立刻抖起来。他扔掉烟头目露凶光,两片嘴皮子不停地颤动,臭娘们,还以为你有多干净,原来背后偷人,给老子戴绿帽,想要钱,一分没有,要拳头,现在就给。他冲过去一把揪住赵芳草的长发,拖着她往墙上撞。小武的手下意识地抱住头,那天他才被人拽去撞墙。赵芳草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抓住吕光明的手就啃,像啃玉米棒。吕光明发出痛苦的呻吟,只好撒手,跳到一边,看着血渗渗的胳膊大口大口地喘气。
儿子,帮爹揍扁这个臭娘们,她偷人哪!吕光明用眼珠子和下巴支使着小武。
赵芳草朝地上啐了一口,那气势就像吐掉吕光明身上的一块肉。她抬起头,让目光狠狠撞击着小武的脸,儿子,还愣着干啥?快去厨房给娘抽把刀,看我宰了这负心汉。
小武望了望父亲,又望了望母亲,双腿不停地打颤,忽然放声大哭起来,那声音撕心裂肺,惊天动地。他一下从两个发愣的大人中间穿过,冲出大门。
11
小巷的半空漂浮着饭菜的香味,天边已经收起了最后的一丝光亮。小武沿着逶迤的深巷哭泣着,脚底飒飒发响。他跑上河堤,黑暗笼罩着田野,河水泛起了幽暗的光,放鹅的哑巴正用竹竿拍打着水面,甩出一串串白亮亮的水珠。那些鹅逆着流水,向码头聚拢。夜风猎猎地飘荡,堤上长草倒伏,有一群红蜻蜓飞来飞去,像在宣告台风即将来临。小武对着河水怔了一下,看着它悄无声息地流淌,然后又跑起来,猛地发力以骇人的速度顺着它们的流向奔跑,他觉得自己就像要挣脱一切,又像要奔向某种东西。中途他绊倒了好几回,又爬起来继续跑。跑着跑着,四周寂无人影,只有耳边风声呼呼。他的脑子里逐渐明净起来,光亮起来,就像那一夜守护着他、给他温暖的那个橱窗,他仿佛看见那些婀娜多姿的模特们走动起来,面带笑容,特别是那个像极了赵芳草的女人,正笑盈盈地朝他招手,随时以母亲的姿态将他拥入怀里。
作者近照
厚圃 ,原名陈宇,号厚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结发》、《我们走在大路上》、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契阔》等,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首届广东省小说奖、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入选“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等。书画作品入选“庄上雅集”八人展(石家庄)、加拿大“东方足迹”中国画三人展(滑铁卢)、2015年亚洲美术双年展(香港)等,曾获2015年亚洲美术双年展(香港)银奖等。
备 注:
● 本公众号欢迎志同道合的文友投稿,文责自负;
● 本公众号对自由来稿有编辑修改的权利;
● 本公众号所提供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网页、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图表等,版权所有,转载须注明出处/来源。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伊通签字笔价格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