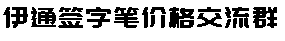
2020-10-02 10:03:55
一
Tony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澳大利亚人。我们算不上朋友。
第一次见Tony是三年前,在旧金山的一个展览会上。那时我刚刚上班三个星期,是在美国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Tony当时是我们公司在澳洲代理公司的一名雇员。他四十来岁,有点发福有点谢顶,但衣着考究。西装笔挺,衬衫全部是浆过的,领部袖口还饰有配套的白金镶钻别针,浑身上下散发着Gucci男用香水味儿。
他好象从没有正经的时候,总是不停地拖着长长的腻腻的澳洲腔儿讲笑话,表情丰富,一双天真无邪的蓝眼睛随意游动在颧骨和发际之间。要是有人说他是英格兰口音,他总会反驳说他其实是苏格兰口音,好像特别地在意自己的血统。
虽然嘻嘻哈哈,他却非常重视细节。展台的全部产品都被他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地重新摆过一遍;有时他还会从某个女同事的套装上捏下一根头发,再轻轻地扔在垃圾桶里。吃过午饭,他总会要一杯漂着白沫儿的咖啡,把餐巾铺平,对折两下,再缠在滚烫的杯子上,然后举起来小口啜饮。每次饭后回展台前,他都会去洗手间用牙线清理牙齿,再含上一颗薄荷糖。
Tony对业务很在行,展览会上他滔滔不绝谈笑风生地给客人介绍产品,最后总能让他们列一个长长的订单,再乐滋滋地把信用卡交给我们。
吃午饭时跟他闲聊,我才知道他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还在哈佛进修过。他跟我说他很喜欢纽约、他所住的悉尼和一切大都市的生活,宁愿去死他也不会离开大城市的。
晚上撤展后,如果不需要陪客户的话,我们几个同事就约好一道吃饭。可是一到晚上,就再也找不着Tony了。
展会结束的那天晚上正好有一场橄榄球赛,同事们就一块儿起着哄去一家旧金山有名的酒廊,想好好放松一下,还死乞白赖地拉上了Tony。
等了半天出租车也没来,老板数了数人,然后就用手机打电话叫了一辆加长的林肯轿车,八个人正好就都坐下了。等车的时候Tony一直在贫嘴,上了车后他又从转角沙发旁抄起电话,假装一本正经地给克林顿总统打电话,我们捂着肚子笑作一团。
这间酒廊座落在一家饭店的顶层,三百六十度徐徐旋转,旧金山的万家灯火就慢慢出现在落地窗外。远处金门大桥上的车流象是一束斑斓的光纤,传递着迎来送往的故事;从渔人码头的喧闹岸边,仿佛隐隐传来街头艺人的阵阵鼓声。
球儿赛得很激烈,人们不停地欢呼、击掌、干杯、添酒,把跟球赛有关和无关的情绪都歇斯底里地发泄出来。 球比完了,人们也都有了些醉意。从始至终,Tony一直很兴奋,几杯酒下肚儿后,话更多了。
这时候,一个爵士乐队开始演出。Tony忽然拉起了一个女孩儿在舞池里跳起舞来,他身体超重,舞姿却十分轻盈,飞速旋转却仍保持绅士风格。他越跳越起劲,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四周的酒客们不断鼓掌喝彩。
突然,Tony跳上舞台,拿起麦克风跟着乐曲唱了起来,伴着身体有节奏地扭动摇摆。他不时地把话筒递给键盘手让他唱上两句,观众们都有节奏地拍起手掌。然后他索性把话筒交给了键盘手,即兴弹起了钢琴,居然动作娴熟,与其他乐手配合默契。我真是大吃一惊。观众们更加沸腾起来,频频碰杯,口哨声呼喊声不绝于耳。
一曲终了,贝司手递给Tony一只话筒,自己拿起另一只,一问一答地和他说话,他还是那么嬉皮笑脸,逗得在座的人前仰后合。酒廊声音嘈杂,加上Tony口音很重,他们说的话我有些都没听懂。
后来Tony干脆让键盘手彻底下岗,自己坐在了钢琴凳上。他疯狂地弹着节奏强烈的爵士乐,乐曲开始、中间、 结束,他都会适时地调笑几下,纯粹英国式的幽默,全场乐不可支。在一曲曲超级动感的音乐里,人们都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座位,在舞池里狂舞。Tony把键盘越弹越快越弹越响,人们都兴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 只听钢琴上一声巨响,然后嘎然而止,连乐手们都吃了一惊,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愣住了。
Tony头也没抬,轻按十指,酒廊里瞬间传出了轻柔古典的“月光奏鸣曲”,象一股清泉流入人们燥热的心里。 人们成双成对,环腰揽颈,轻挪双腿。酒廊的灯一下子都灭了,只剩下一个个小圆桌上漂在宝蓝色玻璃水杯里的盈盈烛光。
一束灯光射在Tony的脸上,手上。他目光凝重,深情款款,好象是在喃喃地向远方的情人倾诉思念爱恋。
曲子结束了几秒钟,大家还默默地站在舞池里。
这时,灯被全部打开,人们又鼓起掌来,Tony满面笑容地站了起来。酒廊的老板适时地走上台来,说实在抱歉,我们应该在一个小时前就关门了,但是我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共度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他把一件酒廊的纪念T恤送给了Tony。
我们也站起身准备撤了,Tony从台上走下来,向我们走来。他不时地被路过的人拦住,说几句笑话。后来我们看见一个女孩忽然抱住了他的脖子,在他嘴上狂吻起来。Tony一边翻着白眼对我们作鬼脸,一边尽量躲着,样子很滑稽。
同事们“哗”地一下儿笑了,有一个还说,“错了,弄错了!”
我有些纳闷,“什么错了?”
那个同事吃惊地看着我,“你不知道Tony是同性恋吗?”
我瞠目结舌。
后来一想,难怪一到晚上Tony就失踪呢,旧金山可是世界著名的基都(同性恋城〕啊。
大家醉醺醺地站在凌晨的街上打车回酒店,Tony晃晃悠悠地走到饭店前面停着的一辆出租车前,拉开车门一屁股就坐在了驾驶座儿上,把站在不远处的司机吓了一跳,赶快跑了过来,以为Tony要偷他的车。原来在澳洲,方向盘是在车的右前方的,Tony喝高了,已不知今宵酒醒何处。
二
出国以前,总是听到很多夸大其辞的所谓“中美文化差异”,。来美国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我越来越觉得其实人都是差不多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有七情六欲和各种毛病,比方说对于“传闲话”的热衷。
刚刚搬到我现在住的这个城市时,我自己住一套公寓。有一次我连续出差两个星期,从机场回到家里,一进门却踩到了一滩水里。原来是我不在的时候,有一根水管因为老化裂了个口子,水就滴滴哒哒地流了一地,把地毯都弄湿了。第二天一早我要去物业去汇报情况,就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说要晚去一会儿。等半个小时后我到公司,房子被淹的事已经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走在楼道里碰到所有人,包括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问我有关公寓的事情,让我着实惊讶不已。在我的印象里,工作时间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老板面前表情庄重马不停蹄,真不知道这些小道儿消息是怎么在瞬间秘密地传到公司各个角落的。
我是年轻小伙子,又是外国人,也不怎么和公司里的老娘们儿们瞎搀合,所以我听到的流言蜚语可以说是不甚了了。即便是传到我耳朵里的,估计也是被别人的舌头根子嚼得淡而无味的了。一传十,十传百,第一百个人真是没的再传了,憋在肚子里又实在难受,于是忽然眼睛一亮看到了我,就哗哗哗地全倒出来给我听,图个自己痛快,总比刨个坑儿自说自话强。我也就没办法只好当这个精神厕所。
Tony失恋的事儿我就是这么听说的。
据说Tony以前有个男朋友,好了很多年,最近突然分手了。他非常痛苦,几天都没有上班,具体的情节我也没太记住。
可是那段时间,Tony好象是化悲痛为力量了,工作业绩非常出色,喜报频频从澳洲传来。尽管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差,可他每天都要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总部上上下下地汇报工作,找不到人还要让前台小姐满公司的传呼,好象是在尽力地引起人们关注。
他还隔三岔五地大老远飞到美国一趟,每次来都关上门泡在几个老板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天。我负责亚太地区,澳大利亚是我的管片儿,可是Tony每次来好象都在故意避开我,不是我当时在出差,就是我在接待其他来访的客户。
他那阵儿还总是向公司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没的提了就有分寸地对工作中的不足发一下牢骚。有一次我接到老板一个严厉的电话留言,说Tony抱怨我发电邮时总把他姓儿的最后一个字母“b”拼成“d”,说这样很不尊重人。其实我是在邮箱的地址簿里就拼错了,所以每次发都是错的。尽管是我不对,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跟我直接说一声不就行了,去我老板那儿扎针儿就有点儿小题大作了,有点儿那个了。
他们说那段时间他的感情生活比较颓废,所以频繁地换男朋友。每次来美国就那么几天,他也能迅速地找到人约会。后来听说Tony看上了我们这儿假日饭店里的一个酒保,是个小靓仔。Tony说特别喜欢他调的一种叫 “长岛冰茶”的酒。到了晚上他要是不参加集体活动的话,大家就心照不宣地说他又要去喝“长岛冰茶”了。
有一次晚上同事们约好一起吃饭,到了餐馆后Tony突然打电话说他很抱歉来不了了,因为他当晚有个约会。 大家都有些沮丧,特别是几个如花似玉的单身女孩儿。
金发碧眼的Kelly喝了一大口酒,哭丧着脸说,“我可真够惨的,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还没男朋友, Tony来了三天就找到一个帅哥。真没劲。”言外之意就凭她这付闭月羞花之貌,怎么还竞争不过一个秃顶的胖老爷们儿,实在是想不通。
拉丁靓女Wonda和澳洲美人Maggie也都跟着显出不份儿,三人唏嘘着互相安慰。
我觉着好笑,就从兜儿里掏出手掌电子记事本,假装按了“日程表”功能键,然后说,“好吧,我就豁出去做回善事,约会你们一道。Kelly,你下礼拜一;Wonda,准备好下礼拜二;对不起Maggie,你只能排到下礼拜三了,除非你给Kelly点儿好处,跟她换换。”
三个姑娘终于找到了发泄对象,对我群起攻之。
已婚的老板看着我孤芳自赏至今未娶,姑娘们待字闺中顾影自怜,只好宽容地无可奈何地笑着摇摇头。
有一天上班,我办公桌上放了一份公司内部文件,是一份委任通知。通知上讲我公司决定在澳洲设立分公司, 由Tony任首席代表。我暗暗吃惊,谁都知道Tony从代理公司的普通雇员升为美国公司的首席代表可以说是 一步登天。我终于知道他最近在忙活些什么了。由于澳洲本是我的区域,这样设了分公司和首席代表从客观上讲是削减了我的权力,这大概是Tony一直避着我和没事找我毛病的原因吧。尽管我对工作上的事不是太在乎,可这也算是我第一次领教了这家伙的攻于心计。
后来我去澳大利亚出差,Tony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梅塞德斯来机场接我。第二天,他又带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是在他悉尼闹市区高尚住宅里的豪华公寓里。我知道他的车和房子都是我们公司提供的,也大概知道他的优厚薪酬。
豪宅装饰典雅,很有格调。Tony红光满面,左手夹着一根凉烟,右手拿着一杯Scotch酒,左右逢源,谈笑风生。
论级别Tony算我的下属,可这时候跟他在一起,我就象一名副其实的碎催。
三
初秋的早晨,澳洲南部的老城阿德莱德,海边,一个古色古香的小站旁,露天咖啡座。
Tony坐在我的对面,戴着一副精制的墨镜,一手慢慢搅动着咖啡上漂着的白沫儿,一手拿着手机,兴高采烈地在和谁聊着什么。
不远处,碧蓝的海浪荡涤着雪白的沙滩,海鸥在低低地飞翔。
一辆小火车到了终点站,车上下来一群老小。老人面带慈祥的微笑,头顶一个鳄鱼邓迪式的草帽;爸爸一手牵着一个小孩,三人咯咯笑着向海边跑去;儿媳一手搀着婆婆,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盖着红白格子布的野餐竹篮。
这是一列单轨火车,铁路从城里一直延伸到海边,沿途经过很多古朴的房屋和教堂,还有一些产酒的葡萄园。
Tony挂断电话,端起咖啡笑着对我说,“对不起,刚才那是我男朋友。这家伙真是疯了,也没打招呼就从悉尼飞到这儿来看我,说是要给我个惊喜。”
“那不是挺好吗,”我心不在焉地搭着腔儿。
Tony也不在乎,自顾自地满脸甜蜜,春心荡漾。
一支亮粉色的风筝在海边腾空而起,象是在瓦蓝的天空上绽放了一朵杜鹃。
两个小孩嘻嘻笑着追着爸爸在沙滩上奔跑,跳着脚儿地抢爸爸手里的风筝线;爷爷奶奶坐在一块淡绿色的塑料布上,微笑地看着孩子和风筝;妈妈开始从竹篮里拿出五颜六色的食品,和一瓶红酒,然后又拿出一个布撑, 一针一线地开始刺绣。
Tony顺着我的视线瞟了一眼,又喋喋不休地说,“基督,这段时间真是太忙了。这个展览会结束后,我又得开始着手准备协会的狂欢游行了。”
我就问,“什么协会和游行啊?”
Tony瞪大眼睛夸张地说,“你不知道我们一年一度在悉尼的全世界同性恋狂欢大游行吗?告诉你,我还是澳洲同性恋者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呢。那是在快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们协会没有几个人,现在简直是数也数不清了。”他说着从钱包里拿出他的会员卡,自豪地给我看。我看到会员编号那一栏,赫然写着000003。
他继续兴奋地说,“每年大游行时简直是太热闹了!你知道我就喜欢热闹。人山人海,全世界的人都来了,协会成员,亲朋好友,还有好多看热闹的,什么好玩儿的人都有。去年游行时,我是站在第一排挑大旗的,国家电视台转播时给了我好多镜头呢。那几天的机票都是要提前一年订的,你要是在协会没有认识人,就是想付四五百美金住一晚都找不到酒店。怎么样,你来不来?或是你的朋友们?我帮你安排。”
我连忙说,“谢谢你Tony,这个就算了,你要是2000年奥委会的人我没准儿就来了。”
Tony满不在乎地耸耸肩,“没关系,你要是改变主意的话,来个电话就行了。”
这时候,一辆小火车进站了,开始在一个小转盘上调头。我赶紧说,“Tony,咱们得走了,开展时间快到了,还得去房间换一下衣服呢。”
Tony在咖啡桌上放了几块钱小费,又对吧台后的男侍挤了挤眼,然后随我上了火车。
四
四十分钟后,我、Tony和几个澳洲的同事西装革履地站在会议中心的展台前。我在美国时见过的Maggie也在这里。
我们之所以可以从容地到海边吃早餐、散步,是因为这个在澳洲的展览会是早上十点钟才开始的。接到会议通知时,我一看日程安排就乐了。
10:00AM:开展
10:45AM-11:00AM:上午茶
12:00PM-2:00PM:午餐
3:00PM-3:15PM: 下午茶
4:00PM:撤展
三天半的会中间还休会一天,用来参观历史古迹和到四五个葡萄园品尝各种美酒。在展会上,我感觉没多一会儿就被同事们叫去喝点东西,吃块奶酪蛋糕,然后就收摊儿吃晚饭去了,完了还要去酒吧接着玩儿。即便是工作时,大家也都嘻嘻哈哈地没个正形儿。
据说欧洲人也这样儿。实话讲,我喜欢这样儿。
后来筹建澳洲分公司时,我在悉尼、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常驻过几个月。每天早上没上多会儿班儿,楼下就开来一辆花里胡哨的零食车,叮铃叮铃地响着小喇叭儿,然后同事们就都下楼吃东西、抽烟、聊天儿。吃完午饭没多会儿,零食车就又来了。
在美国可就不同了,不光在办公室忙得四脚朝天,要是遇上展览会,早上8点一进会场,到晚上6点撤展,几乎就没有一分钟闲的时候,连上厕所都要一溜儿小跑儿。中午饭大家轮流去会议中心的小吃部啃个三明治,吃完还要给公司打电话查留言,并处理办公室的一些急事。一天下来,皮鞋里的双脚疼痛钻心,浑身乏力。撤展后还要陪客户吃饭,要是碰巧有本公司赞助的招待晚宴或是鸡尾酒会,还要端着个酒杯,咧着嘴哈哈哈地假笑着,再站四五个小时。
有一次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吃饭,谈到了每个人自己的梦想。轮到我时,我老老实实地说,“我的梦想是每天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不被闹钟吵醒。”
一桌的美国同事都张大嘴作惊奇状。
我当时心想我还有另一个梦想没告诉你们呢,那就是不跟你们这帮假模假势儿的傻B一块儿上班儿。
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我的直言,从此落下一个外号--“瞌睡虫”(Sleep Master)。
后来他们不但在人前背后叫我“瞌睡虫”,还不断收集证据。比如说在台湾出差赶上地震,我呼呼大睡愣没被震醒;还比如说我一上飞机就吹充气枕头,保证在飞机起飞之前,头一歪酣然入梦。有时几个同事一起飞,一落座他们就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只要一看我从包儿里掏充气枕头就捂嘴偷偷窃笑,包括我老板。
有一次我早出晚归地陪一拨客户连陪了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除了在公司里没完没了地培训、谈判,天天在佛罗里达的大太阳底下打好几个小时的高尔夫球,晚上冗长的晚宴完再去酒吧,周末还带他们深海钓鱼吐的稀里哗啦。到他们走的时候,我已是精疲力尽面如菜色。一个女同事说, 他们走了你该高兴得跳踢踏舞了吧。老板马上接着说,对,没错,他肯定跳着踢踏舞就径直上床了。说着还晃着身子眯着眼睛蹦跳着往前走了几步,学我迷迷糊糊欢天喜地上床睡觉的样子。还真是,我一到家就倒头便睡,睡了几乎一整天。
在美国时过不了多一阵儿,我们就会接到Tony的传真说他要休假,有时候能长达一个月,说是澳洲政府规定的。他们休假时从来不查传真、电邮和电话留言。即便是他们上班,有时候我们打电话也找不到人。有一次老板气得说,这帮澳洲、欧洲懒蛋,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就开始人手一杯鸡尾酒了。
有一回Tony休了几个星期的假回来,打电话跟我说,“我的假期舒服极了,哎,你什么时候休假啊,要不要来澳洲啊?”
我想了想说,“哦,我两月前好像有过一天调休,你要是早邀请我,我就连夜去一趟悉尼了。”
对不起,有点扯远了。
我想说的是Tony住着豪宅开着靓车拿着高薪还什么都不用干,这差事真好我真想要。
我还想说我是懒人想睡懒觉向往懒散的生活可我做不到所以我很搓火也很无奈!
五
一个犹太人模样的客户走到我们的展台前,很有兴致地开始摆弄那些展品,我连忙上去打招呼。看了看他脖子上挂着的胸牌,我于是问道,“XXX医生,您是从墨尔本来的吗?”
“对啊,你们公司在墨尔本有销售人员吗?”
“有的,有的,”我赶忙叫身后的John,他是我们在墨尔本的分销公司的代表。
John热情地和犹太医生问好,又互换了名片。然后,他开始耐心地讲解各种产品的用法及优点,又一一地演示。客户显出很有兴趣的样子,频频点头,又提了很多问题。
根据犹太医生的要求,John拿出一张订货单,一项产品一项产品的往上填,一会儿就列了一满片儿。我们都觉得John今天要作一笔大买卖了。然后,John把产品编号和数量迅速输入展台里的电脑,电脑里就自动算出了报价。他把报价单打印了出来,递给犹太医生。
医生看了看,马上摇了摇头说,“太贵了,我开的是私人诊所,这些器械价钱太高了,你能不能给我10%的折扣,否则的话我就不买了。”
John有点儿为难,因为他没有权力给打折,他需要Tony的许可,但他答应试一试。
John把Tony悄悄地拉到一边,没想到他一提Tony就说不行,说这些东西已经够便宜的了。John又试着说服Tony,俩人在一起嘀嘀咕咕地交涉了两分钟,John回过头来时,脸色很难看。他尽量表情自然地走回展台,客气地对客户说很抱歉我们不能降价,犹太医生果然说了声“谢谢”就走到我们竞争对手的展台去了。
我很为John可惜,因为他要能作成这笔生意,就可以拿到可观的佣金。Tony和我都是领工资的,而John可是靠佣金度日的,包括这次参展来的酒店、机票和其它费用他都是要自己负担的。况且大家都知道,在展览会上给10%的折扣是非常正常的。可这是他们澳洲分公司的内部管理,我也不好多介入。
客户走后,John就小声儿嘟囔着,“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报价太高,在澳洲根本没有竞争力。这也不光是我个人的事,眼看着客户一个一个跑掉,对公司有什么好处?”
Tony听到了,就搭了句腔,然后俩人居然话赶话地小声争吵起来。好在当时医生们都在会议室里听一个讲座,展台前除了同事没有别人。
John人高马大,是业余橄榄球运动员,又喜欢喝酒,所以脾气较暴,他最后不知道说了句什么,然后红着脸走了。
Tony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手机,向咖啡站那边走去。
我们都很尴尬。我问Maggie,你要不要咖啡,我去拿一杯。Maggie笑了笑说,“不用了,谢谢”。
我走过去端了一杯咖啡,放了块方糖,就往展台走去。Tony在咖啡站边的一个大柱子旁打电话,背对着走廊。
路过他时,我忽然听到他说,“这次展览会John表现非常不好,讲解产品时敷衍了事,,我觉得你该好好和他谈谈了,不行就让他走人。”
我心里“咯登”一下,我想这肯定是Tony在向John的老板上眼药儿。操。
回到展台,我看到Maggie和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在说笑着,看到我,她就给我介绍说,“这是Kevin,Tony的朋友。”
Kevin彬彬有礼地向我问好,声音浑厚而文雅。他脸膛红红的,一看就是经常在海边日光浴或是作各种户外运动。
这时Tony走了回来,他一见Kevin就笑着故作嗔怪,“突然袭击呀你,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啊。”
Kevin就宽厚地笑了,冲大家挤了挤眼,还有一点点得意。
Tony看了看表,对我和Maggie说,“快撤展了,你们帮我照应一下,我先去帮Kevin安顿下来,咱们晚饭的时候见。”说完就和Kevin亲亲热热地走了。
Maggie看着两个人的背影对我说,“你知道吗,Kevin还是悉尼市有名的大律师呢。Tony这次象是真的找到意中人了,他还跟我说要跟Kevin厮守终生呢。”
我心想,该不是又一杯“长岛冰茶”吧。
晚饭的时候,我们来到一家海鲜餐馆。Tony、John和其他同事都来了,Kevin没有来。
点菜时,Tony跟我叫板,问我敢不敢要澳洲产的一种硬壳的海虫子。我不但要了,还当着他们的面儿一个一个都吃了, 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我心想,餐馆里除了桌椅板凳,我什么没吃过呀。
John虽然不再生气了,可还是有点别扭,所以话不是很多。Tony却象没事人儿一样,他坐在John的旁边,搭着他的肩膀,还不时地和他开玩笑。
我看了看Tony,心说这丫的可真阴,够孙子的。
六
不久前,公司里爆发了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Tony辞职了。
在我们国际部,这可就算是头版头条了,谁都知道Tony的职位可是多少人都垂涎欲滴的啊。
他的辞呈大家都传阅了,我也看到了。这封传真主要分两部分阐述他的辞职原因,第一部分他措辞很职业化,主要是一些工作上的原因,比如竞争过于激烈、人事管理困难等等,但好象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勉强说辞;第二部分他却写得很情绪化,象是一封真情流露的家信。
他写道:“我之所以辞职还有一些个人的原因。我亲爱的伴侣(Partner)Kevin最近身体不适,刚刚被诊断出患了不治之症,时不多日了。根据他的愿望,我们准备离开悉尼,在一起共度最后一段质量时光。我已经在澳洲北部一个安静的海滨小镇买了一个小酒馆,加上我的一些积蓄,应该够我和Kevin生活了。我也找了一幢面海的房子,Kevin喜欢大海。
我视和你们一起工作的时间为一种容幸和一种愉悦,但30天后我就要结束这里的工作和在悉尼的生活了。对这匆忙的告知和与之带来的不便我感到万分抱歉。
最后,愿上帝保佑你们,还有我的Kevin。”
放下传真,我感到脑子里有一点乱,“Kevin得的不会是爱滋病吧,他看上去人很好啊。Tony有没有事儿呢?他也应该去查查吧。这份工作Tony真的说不要就不要了?再说他那么喜欢悉尼,他说过他死都不会离开大城市的。Kevin还能活多久呢,他去世后Tony怎么办呢?”
想到这儿,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我赶忙接起来,“你好,这是XX公司XX,我怎么帮助你?”
是个客户打来的。
大公司里人事变动很正常,Tony的事大家也慢慢不再提起。
几个星期后,同事们都接到了Tony发来的一个电邮,是一张房子的照片。
这是一座两层的木制小楼,木板呈灰黄色,显得略有些陈旧。房子座落在海滩边,一层有一个车库,二层有一个与房子等宽的伸出的大大的平台,面向大海。平台上有些花花草草,两把躺椅,中间一个咖啡桌,和一把撑起的海蓝色大沙滩伞。
屋里的摆设看不到,想必也是舒适温馨的。
屋脚下靠海的一边,有几束枯黄的芦苇,在风里微微倾斜着颤抖着。几分安祥,几分凄凉。
在我的想象里,Tony现在这样生活着:
他白天照顾好Kevin就来到小酒馆,手里拿着个酒杯,与小镇里一些老酒客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应酬着。傍晚时分,他关门打佯,驱车回家。在沿海的小路上,他打开车窗,任海风吹进来,断断续续地吹着口哨,有点疲倦,有点怅然。
回到家里,他又打起精神准备晚饭,然后给Kevin喂药注射。收拾停当后,他给Kevin的腿上盖条毛毯,然后用轮椅把他推到面海的平台上,有一搭无一搭地讲讲白天酒馆里的事情,一起看着如血的残阳一点点沉入海中。
每想到此,一股游丝般的敬意都会在我心中悄悄升起。
Tony辞职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可能以后也再没有机会见面了。我说不上喜欢他或是讨厌他,他只是我生命里的又一个路人。我们不算朋友,可我也希望他一切都好。
相关推荐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23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伊通签字笔价格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