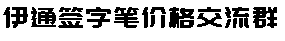作为一棵出生在普洱的树是幸福的。
那几日,我心里反复地念叨这句话,羡慕,且酸溜溜,像一位总被呵斥的孩子抱怨妈妈对其他子女的偏爱。
大自然对普洱是娇宠的。
我的生地平原,是一览无余的明信片。这里的大山却是加厚的情书,密封着太多活蹦乱跳的爱恋,或羞羞怯怯千回百转,或泼泼辣辣单刀直入,或疏疏淡淡灵犀一点,无边心事,寂寂相思,只给有情人阅读。
出发前,看卫星地图上的普洱地域,群山拥挤,如方桌上摆满了箬叶裹缠的绿色粽子;穿行其间的公路像巧妇手中银针带飞的丝线,在“粽子”的缝隙里优雅地游向远方。有关材料讲,普洱地区绿化率高达百分之七十许。我极力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想象一个无色无味的数字背后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棵小草的日常。
晚上十点多,透过飞机舷窗,看到一片倾立的万点灯火,如同巨大的夜幕上浮着一只方舟——普洱市以如梦似幻的形象出现了。我知道一定有大批大批的树在仰望,在猜测,在喁喁私语,那一刻,我忽然为自己贸然的闯入它们的家园抱歉不已。
普洱城区像一则短小雅致的小品文,读者的兴致刚刚飞扬起来,它已经收尾了。汽车的灯光里慢慢出现一条曲折幽远的山林公路,公路两边,蜂拥着密密麻麻的树,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独自站着的斜躺在别树身上的相拥想抱在一起的,不论原来正干什么,被汽车的灯光一照,全都停止了说话,我想他们一定在扭着头打量我们。黑暗太浓,在一闪的工夫里,我向每一棵树默默问候。
在城南乐海子山顶的道氏山庄,我们度过了在普洱的第一个夜晚。
迷糊中,听到谁在轻轻拍打身边宽大的落地窗,有一下没一下的,三分迟疑两分羞怯。我朦胧着双眼,问:“谁呀?”轻轻的拍打声中断了,回应我的是窗外一阵啾啾啾的鸟鸣。我爬起来,拉开窗幔,顿时天光大开,对面的青山,山下的普洱城,都被速写出来。可是,窗下只是一面坡地,坡地上不过是些青草芭蕉,没有人啊。一阵透亮的山风吹过来,窗外那棵不知名的树,伸出它的枝丫轻轻点到窗玻璃上来——噢,我是被一棵树叫醒的。我至今不知道它的名字,我想小鸟当时是告诉过我的,愚钝的我没有听懂。它不挺拔,脖子还有点儿歪,枝柯更是不守规矩地左右弯曲,树叶倒是黑乌黑乌的壮。它真的不是什么栋梁之材,甚至做不成一个小板凳,在太多的地方,它的命运只有一个:被砍掉。而且,它还贴着屋檐生长,不怕扫落一片瓦?不怕打坏一片玻璃?它与我隔窗相对,不懂我的疑惑与担心。因为,在这片土地给予的大爱里,它的生长没有委屈和恐惧。
一棵无名的小树尚且如此,我已经可以想象茶树的幸福了。
在平均海拔1700米的营盘山上,大片大片的茶园在云雾里出没,从山脚到山巅,从山巅再到山脚,茶树呈盘香状,一层层盘绕而上又一层层盘绕而下。它们快乐地绵延,向着苍远的天际,向着春天的深处。这里年平均气温15--20摄氏度,“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大自然把最好的脾气似乎都给了这里。我靠近一棵道边最普通的茶树,一阵娟娟细细的清香便迎送过来。它的枝丫随意地搭在其他茶树的枝丫上,向我们炫耀它们之间的亲密。在深绿色的叶片丛里,青色的新芽已经睁开眼睛看蓝天了。
后来听专家何仕华先生说,普洱是茶树的故乡,全世界的每一片茶叶里,都有关于普洱的或近或远的记忆。我想象它们有一天被采下来远离故乡,是不是也会乡愁悠悠?
茶树既然是普洱的摇钱树,我原想,它一定会占据大地更多的宠爱。景迈山的万亩古茶林,却果断地纠正了我。
作者在景迈山古茶林的茶树下
钻进去,最引人注目的是几棵千年小叶榕,顶天而立,像竖在一群孩子中间的几个虎背熊腰的壮汉。这壮汉却脾气温和,手脚都小心谨慎,恐怕碰哭下边顽皮的小朋友。比小叶榕矮一截的有很多种乔木,像赶集似的,漫山闲逛。抢眼的是一种名叫黄金雨的树,满树金黄,亮得晃眼。如果不是普洱的朋友引领介绍,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边还有茶树。
古茶树就在眼前,三五一群,七八一行,散布在大树后、小树旁。几百年来,它们都是这样,普通得像蹲在路边抽烟的老农、弯腰在溪边浣衣的村姑、负柴而归的樵夫、绕着山花躲迷藏的顽童,一点儿看不出“山主”的傲娇气派。倒是那些石斛啊茯苓啊许许多多的药草,会任性地拦住我们这些陌生游客的道,逼着我们一次次绕开。这里属于每一棵树。
阳光正在哺育整个山林,我仿佛听见生命的轻柔的吮吸声。导游李先生提醒我们,此刻,我们呼吸到的空气里负氧离子大约为一万多个,小心醉氧。醉氧?我当时就想对着山林中的每一棵树发问:你们知不知道,在同一时刻,城市的行道树正奴仆一般被勒令肃立在道路两旁,低头垂眉地在被汽车尾气羞辱?它们也是树,肺里胃里却全是人类的罪孽!它们的生已是这般卑贱,砍伐的刀斧仍时时在它们头顶高悬——也许因为街道改造,也许因为官员不喜欢,也许根本没什么因为。
在茶林的一处,我见到几段倒地的硕大的古木,三四丈长短,两合围粗细,不少地方已经朽得土木不分了。它们倒在它们生长的地方,回归大地,神态安详。当初它们倒下时,必是修房建屋的大用之材,为什么没人运下山呢?普洱的朋友郑重地告诉我们:山民们信奉万物有灵,认为每一根草每一朵花每一棵树都值得尊重。他们绝不会去打扰一个需要安息的灵魂的。
哦,有尊严的死亡,和有尊严的生一样,都应该是神圣的礼唱。
那一刻,我明白作为一棵出生在普洱的树为什么是幸福的了。
作者简介:
谢国有,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早年有散文.诗歌、小说、评论散见于各级报刊。近年多关注现、当代文化人物,已出版《一个人的百年孤独》、《吴清源传》《邵逸夫和他的黄金时代》等。
更多精彩
欢迎关注
字游网站
www.wordtour.hk